桃李自言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半壶纱ylyynk.net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这事儿自然也是有理由的。
林宣拱了拱手,道:“随吴兄而来,不敢推脱。”
他语气颇叹惋,好似不能在家里安心复习,是多么令人悲痛欲绝的一件事,钱正岚不吃这一套,闻言,冷笑了声:“吴庸吃屎,你也跟着吃吗?”
远处的吴庸没来由的,眼皮跳了跳。
一语惊人。
一边的贾琏简直惊呆了,他呆呆站了半晌,左看看,右瞅瞅,还是难以想象刚刚如此粗鄙之语,竟是从一方教育大员口中蹦出来的,偏偏林宣倒是接受程度良好的样子,内敛谦和地笑了笑,应答道:“他吃他的,我自然是不会碰的。”
钱正岚听了,捋了捋胡须,点评道:“还没傻透。”
钱正岚身材修长高大,纵然年龄已至暮年,脊背依然挺得端直,单看背影当得“渊渟岳峙”四字——大凡只要是中得了进士的,便几乎没有丑人。
他壮年摘得进士,早年在御史台做言官,其人直言耿介、英悍彪爽,整个朝野都有耳闻,此后也因为这张嘴,数年都在京里打转,一直不得重用,此后归原籍为官,也算是暮年最后一程官途。
钱以纶在尽力维持文会的秩序,正主钱正岚却并不着急,他慢悠悠向前踱了几步,看着悬挂在墙上的举子诗作,或走或停,看了一会儿,见林宣还在原处站着,眉头倒竖,喝了一声:“过来。”
林宣方才跟上。
这一面墙上皆是悬挂的竹榜的诗作,檐角错落,林宣随钱正岚的目光仰头望去,雪白的宣纸上尽是漂亮的行楷字,是专门负责抄录的文馆书生所写的,远看宛如蝇头,整齐干净,最右侧的桌上,不知是谁画的一张山水图,青铜狴犴瑞兽压的镇纸,漂亮极了。
江苏自古出进士,江南半壁皆是仕宦之家,积年累月此般内卷下来,便是普通士子,也是能诗能画之辈。
——什么都缺,就是不缺读书人。
而能从各州府,通过科举考出去的,不说德行,才能势必需要鹤立鸡群。
钱正岚精于策论、长于诗歌,只是扫了一眼,便叹气:“一个个所做之诗,忒俗、忒俗。”
贾琏随林宣过来,见林宣和钱正岚盯着墙上张贴的诗看,也照猫画虎地抬了头,他看得晕晕乎乎,实在看不出好歹来,总觉得什么诗都一样。
他念道:“亲民之官,莫如知县。循名责实,谓能知一县之事也……”
念到一半,突然回神。
钱正岚回首,似笑非笑望了贾琏一眼:“这是去年如皋修县志时的留本,呈来盛华楼好好保存的,其知县题的序,因其字华美丰沃,因而张在楼里,并非今年文会之诗。”
贾琏有点尴尬,连说:“是、是。”
钱正岚没再理贾琏,转头问林宣:“你如今可会作诗了?”
林宣道:“还是不熟。”
“意思是会做?”钱正岚挑了挑眉,“那倒也好,后日的府试,等张榜后我要看你的卷子,今日暂且饶过你,届时便是见真章之时。”
不用林宣多说,钱正岚也大概知道他的水平,在文会上作诗的少说也是举人起步,他倒并不勉强林宣今日也要跟风做一首新诗,右手挥了挥,示意林宣:话说完了,滚。
林宣麻溜地滚了。
·
盛华楼人潮熙攘,不过片刻,便又是两首诗张榜。
吴庸忙着应付南安郡王,兼之他还有诗要作,以此对峙。贾琏先行上了二楼,显然是对斗酒投壶兴致更大,林宣倒是难得闲暇了下来,兀自站在楼檐下站了片刻,望着远处发了会儿呆。
今日来到文会,他并非没有事儿做的。
他想试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
林宣抵着光洁的墙面,掏出不知道从哪里顺来的纸和炭笔,不怎么工整地写出来一个字儿:苔。
这首小诗存在他脑子里,存了大约两年多的时间,是袁枚那本残缺诗集中的一首五言小诗,他偶尔翻一翻,已是滚瓜烂熟,闭着眼都能倒着写。
此刻没过一分钟,便写完了全诗,在诗后工工整整标注了名姓“袁枚”,随纸递交给专职誊写的书生。
到处都是人,书生忙得顾不得抬头,只勉强看到一双骨节分明、白皙而年轻的手,说了声知道了,将纸展开,大致浏览一遍内容,突然顿住了。
“……咦,《苔》?”
来盛华楼里作诗的,大多挥挥洒洒写尽楼之华美、诗会之盛、景之妍丽,一个“苔”字却实在不常见,誊写的书生只觉得有趣,回了神,揉了揉酸痛的手肘,不自觉跟着念了一遍: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
短短四句,写得生动活泼极了。
这首诗并不难理解,甚至在一众佶屈聱牙的诗作中显得过分简单,像是莫扎特安魂曲旁边的凤凰传奇,迈巴赫边上停放的电瓶车,透着股格格不入的质朴味儿,书生甚至还没看完全诗,便完全理解了诗的涵义。
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,依然有
![来了[悬疑]](http://ylyynk.net/images/2812/c66fef42f9ae91c7f971a8ad200f684d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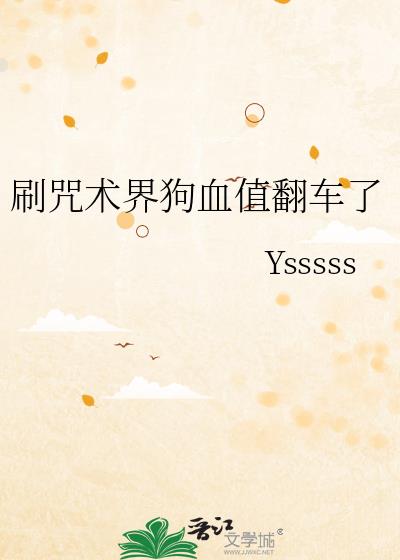



![胡同里的老姜一家[年代]](http://ylyynk.net/images/3147/9af4360d047f5995095928226dd4868b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