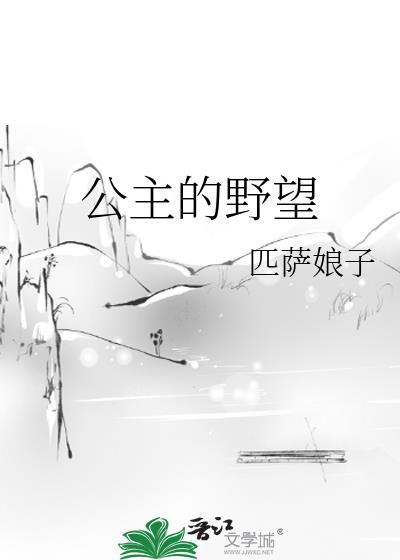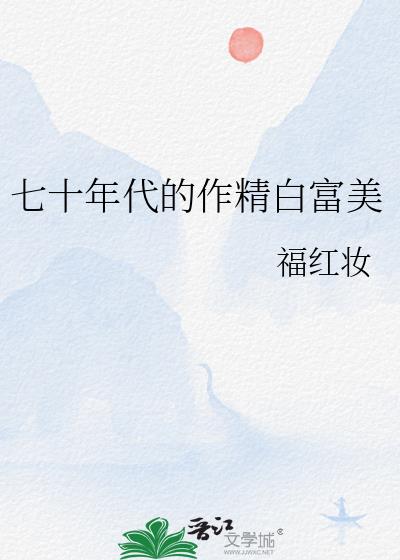骑鲸南去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半壶纱ylyynk.net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项知节眼神里流露出真切的困惑, 仿佛不懂他在说什么。
半晌后,他的困惑过渡为平和:“虽不知你为何要说‘问心无愧’,但你与我确实相像。……胆子都不小。”
他一应情绪, 皆是收敛得滴水不漏。
闻人约躬身行礼:“草民冒昧。”
在低头的一瞬, 他想,若顾兄非是四年前死去的乐无涯,自己这样说, 确实是过于冒犯了。
可若是自己猜对了, 那么,六皇子的心思和城府,就堪有天之高、海之深了。
“起来。”六皇子并不恼火, “我只是好奇,你如何敢这般和我说话呢。”
“太爷教过我,人无倚仗时, 需得借势。”
“你借谁的势?”
闻人约坦率道:“借太爷的势。”
“……方才六皇子问,我是谁。回六皇子,我是南亭县令闻人明恪的学生,亦是他的挚友。除此之外, 我一无所仗,也一无所倚。”
这话他说得真诚恳切, 发自肺腑。
他是死过一次的人了,如今身份更易、相貌全改,世上唯有顾兄一人知道他究竟是谁。
闻人约清楚,自己现下的言行举止,堪称放肆。
可顾兄于他而言, 是独一无二、绝无仅有的。
无论是皇子还是将军, 他都不可相让分毫。
“人若无势时, 借势是常理。智者借力而行,慧者运力而动,荀子亦有云,‘君子善假于物’。”
项知节话音依旧柔和平稳,如他名字一样,进退有节。
“……可是,势借一时,不可借一世。人到底是要自立。盼你能立志建功,有朝一日,能与他比肩而立,共为百姓翼护、朝廷臂膀。”
闻人约顿了一顿:“多谢六皇子勉励。草民务当为之。”
一场和平的对谈就此结束。
项知节起身出院,依习惯练习太极剑,以此养生。
闻人约来到书桌前,挽袖研墨,预备写乐无涯布置给他的文章。
但六皇子的话,在他脑海中盘旋往复,声声入心。
“人到底是要自立。”
“有朝一日,能与他比肩而立。”
是,他能力不济,出身平庸,即使知这官场多艰,也难以护他,自是比不上出身尊贵的皇子,也不及战功赫赫的将军。
要到如何的地步,才能与他“比肩”?
才能和顾兄……相配?
他心思游移,在无知无觉间研出了一大砚的墨。
书房窗外,剑声飒飒,宛若游龙。
项知节的脑中,则盘桓着另一个声音:“回六皇子,我是南亭县令闻人明恪的学生,亦是他的挚友。”
明相照能这样坦荡地说,他却偏偏不能。
他是闻人明恪的什么人?
不能说。
他是乐无涯的什么人?
不可说。
他挥剑破空,却斩不断缭乱纷扰的思绪,索性收剑回身,返回屋中。
……
此时,如风驾着车,顶着一头大汗赶到了县衙门口。
他虽是第一次来到南亭,但无需问路,便能找到县衙方向。
毕竟他不聋。
听着主子的袅袅笛音,他就能辨别方向。
他叹一口气:大早上的就吹上了。
人都见着了,怎么还犯相思病呢。
……
南亭是小城一座,“灭门”一词又确实足够骇人听闻,小半日间,这噩耗便传遍了南亭上下内外。
事关性命,不需官府多加约束,街面上行走的人就变少了。
不及天黑,大半商铺就都上了门板。
向来繁荣的南亭县,难得添了几分萧索孤零之气。
两日后,天将黑时,主街之上,人人不约而同加快了步伐,赶着回家去。
而乐无涯正等候着最后一炉吊炉瓜子。
在氤氲的瓜子香气中,他一面剥着上一炉剩下的几粒瓜子,一面问身旁的人:“……看得不差?”
他吊儿郎当的模样,好像只是在和那人品鉴这一炉瓜子的优劣。
一阵腾涌而出的雪白热雾被晚风吹散,露出了盛有德的面孔,以及他那标志性的、又红又大的酒糟鼻头:“差不了。就是天金当铺。一个人怀里塞了一小包东西进去。半个时辰过去后才出来,怀里的东西就没了。夏日里穿的衣裳单薄,多了什么、少了什么,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
“确定不是南亭人?”乐无涯加快了剥瓜子的速度,“不是哪个本地的败家子赌晕了头,瞒着家里偷了家私来当?”
盛有德笃定道:“太爷放心,南亭家里稍微有点钱的,我们这些行乞的人没有不认识的。那人瞧着确实眼生,走路也歪歪斜斜的,南亭本地绝没有这么一号人。”
“人在哪儿?”
“那人自从酉时进了天金当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