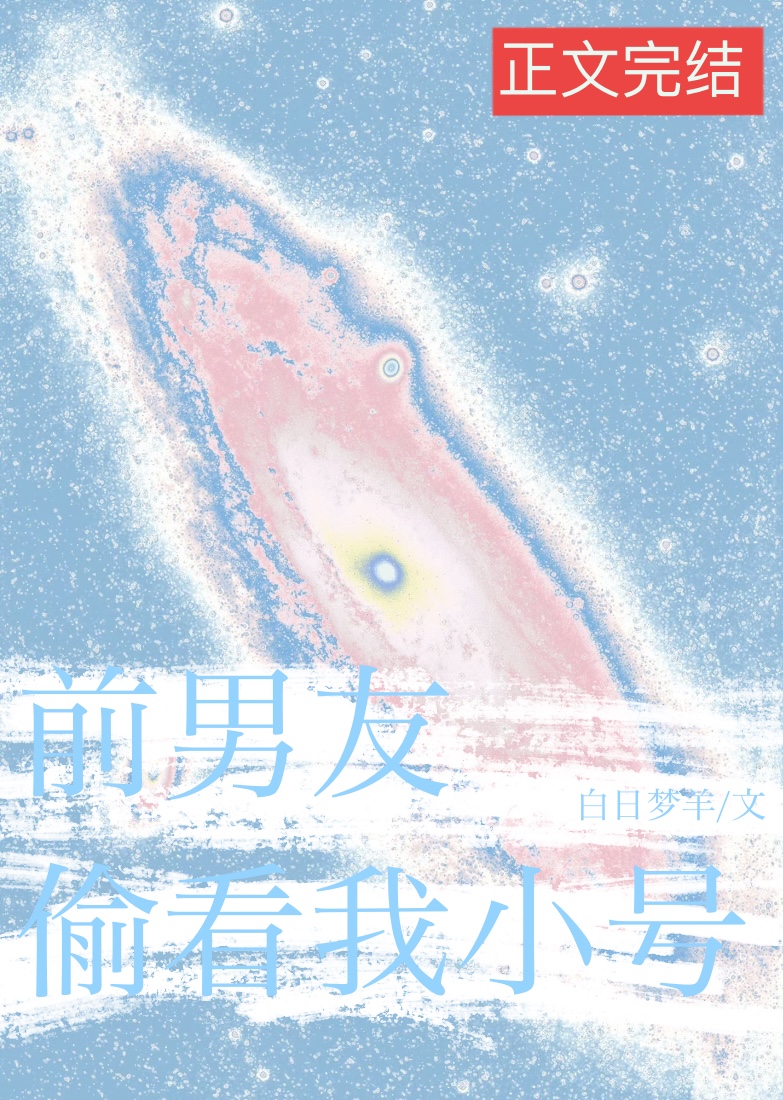听月姚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半壶纱ylyynk.net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丝百福团纹,她盯的眼睛发痛,咬紧了牙关,吞下无数吟哦。但这份安静乖觉并未换来怜惜,身上的男人反而更加狂暴,她细白的一把腰被握出根根指痕。
外面天光渐渐昏暗成晕染的墨色,安宁中间几乎昏过去,但又被很快弄醒,没有喘息的空隙。
事毕,季政掐着她的脖子把她扔下榻,眸色与天光一样沉暗:“滚。”
从殿阁出来,安宁已经是穿戴齐整的模样,她回屋拿了块土布,去水井边沾湿了,躲到净房中给自己擦了擦。
秋日寒凉,她止不住地打着哆嗦,但面上却一直是若有所思的,仿佛惨遭凌虐的不是她本人。
回到房中,夏荷正在和蕊香说话:“不知道是宫里哪个好福气的伺候了殿下。”
照管茶水房,方才那个时辰叫水,她们敏感地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。
见她回来,说的热闹的两人瞬间收住笑,把水盆踢翻在地:“去倒了,把地弄干净。明早我起来看不见面盆架上有热水,你仔细着。”
安宁默默收拾,擦洗到子时方歇,她们也不许她睡在通铺上,只在地上铺张草席凑合,晚间还要伺候三人起夜。
次日给她们提好热水,蕊香指派她去浣衣局拿衣服。
安宁从顺德门一步步丈量魏国皇宫的土地,从前做公主的时候,觉得日月星辰都被框在这宫中方寸之地,不如外面天高地阔。如今做奴婢,倒发自内心地生出禁宫深深殿宇幢幢的感慨。
不过哪怕身上无一处不酸痛,安宁也没有表现出来,仔细看还能从她脸上辨出些不解之色。
去浣衣局,昔日女官语含嘲讽地喊了句:“安宁公主。”
“奴婢是宫人安宁,来取东宫殿衣物。”她敛眉低气,一味忍让。
奚落落难凤凰的癖好被满足后,女官见她一团和软,便没多做为难。
取到衣物,安宁沿着道边走,没注意到身后一直跟着个人。
“十皇妹……”
眉心一跳,安宁从思绪中回转,扭身看向来人。
脚下宫鞋溅着点点黄泥,一身发污的浅粉色宫装,白绢花点缀的双环垂髻,都影响不了她绝世的容颜。安宁叹气,轻声唤道:“八姐。”
“怎么不叫皇姐?”李朝夕迈步上前,恨声道,“这才多久,你便丢下咱们李家的气节,奴颜婢膝地向仇人摇尾乞怜去了?别忘了,你是魏国的公主!”
魏炎帝在世时极度宠爱八公主李朝夕,父皇驾崩后,太子皇兄即位,也对她照顾有加。李朝夕曾经是京城年轻一辈中最尊贵的女子,国破后一夜之间从天翻入地狱,她怎么能接受得了。
“不是了。”安宁平静地开口。
“什么?”李朝夕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“从宫门被破那一刻,我们就再也不是公主了。”季政在大殿中斩下皇帝人头,等于砍去了李家所有人的膝盖,自此她们只能跪着,做人下人。
李朝夕嘲讽道:“好,好,没想到我还有个识时务的聪明妹妹,真对得起魏朝万民的二十载供养。”
“那依八姐意思该当如何?”
“杀君弑兄之仇不共戴天!”
“自国破,为季家辩经的经世大儒、对新主纳头便拜的父兄两朝肱骨、拱手让兵权的武将不知凡几,他们的俸禄哪一分不是民脂民膏,八姐怎不让他们身先士卒做出个表率来,何必为难小妹我。”安宁瞥了她一眼,知道李朝夕这会儿还没适应身份的转变,不欲和她多说,转身便朝东宫去了。
被昔日最温吞的皇妹抢白一顿,偏她还一时顶不回嘴,李朝夕恨声道:“我早晚要为皇兄报仇!为我李家报仇!”
当晚,安宁又被叫去承恩殿,季政左手执笔批着折子,桌边放着太子麒麟印玺。半晌方放下笔,他注视着她,好像要把她整个人看穿:“孤最后问你一遍,李仲玚在哪。”
手指略微蜷缩,感受着指尖痛楚,安宁抬眸,脸上不再是令人着恼的平静,她寥落地回忆那天:“早七天,皇……李任便下令宫中禁严,不许出入。奴婢和其他未开府的兄弟姐妹都在各自殿阁,被侍卫看守着不准走动。直到十一月初九那天晚上,奴婢睡醒看见火光冲天,李任派宫人来传话叫奴婢去守卫周密的正殿。但奴婢怕去了就会被逼殉国,便和奶娘康嬷嬷在内室躲避,未踏出殿阁一步,确不知李仲玚的下落。”
季政手中有名叫陈锋的侍卫的供词,当晚正是陈锋守在她殿阁外,与她所说没有丝毫出入。
安宁注意到他往后一靠,神态比方才放松,他阴冷地嗤笑出声:“孤以为安宁公主忠孝仁义,当欣然以身殉国,原来也会怕死?”
没有任何预兆的,两行清泪汩汩不绝流下来,安宁却连眼都没有眨,她看着季政,似是想牵一牵嘴角,做个自嘲的表情,却没能成功,垂眼轻声道:“自然是怕的。”
有人说眼泪是女人最大的武器,姑且不论对错,安宁也只剩下它了。
能活着,谁会想死。
季政记忆中的红叶,虽


![长嘴小反派的亲妈[七零]](http://ylyynk.net/images/367/18d410c30c9ccd90e0d7bb03becc6917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