尤四姐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半壶纱ylyynk.net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哽声道:“婆母放心,他虽不在了,我照旧还像以前一样孝敬您,伺候您终老。”
余老夫人听后,哭得更是震心,“咱们娘两个一样的命苦,我没了儿子,你也没了父母,往后就相依为命吧,好好支撑门户,千万不能让这门头倒了,惹人笑话。”
也许这就是老夫人的高明之处吧,心里什么都知道,但还是可以忍辱负重,尽力地笼络住她。
如约终究不是个薄情的人,十五那晚余崖岸说出许家灭门时的惨状,她曾想过不欠余老夫人什么,她只是把余崖岸加诸在她身上的痛,照原样奉还罢了。可事儿真出来了,看老夫人难受得这样,她又觉得愧对她,心里像刀割一样。
将来的事态会如何发展,眼下也说不准,但为了安抚老夫人,她自然要答应,“我和您一起撑起门头来,不会让他的心血白费的,婆母放心。”
老夫人连连点头,到底坐不住了,仰身又倒回了引枕上。
顺了顺气,她惨然道:“我听说昨儿皇上来了,我病得起不来,也不能迎接,但愿皇上不要怪罪吧。后头还有王公诰命们往来,咱们要仔细款待,不能叫人背后说嘴。你交代底下人,都打起精神来,别一副天要塌的样子。心里再怎么苦,自己心里知道就罢了,万万不要做在脸上,晓得吗?”
如约说是,“媳妇都记住了。”
老夫人调转过视线,含着泪在她脸上打量了一圈,“难为你,接连经受这样的打击。我的身子又不争气,担子落到你一个人肩上,你小小的人儿,怎么扛得住。”
如约替她掖了掖被角,温声道:“您别担心我,只管养好自己的身子。衙门里派人来主持丧仪了,叶大人也在呢,您只管放心。”
老夫人轻叹了口气,“这位叶大人,想是要接替元直的职务了,咱们得和他打好交道,说不定将来还有劳烦人家的地方。”
她面面俱到,想得十分周全,并不因丧子之痛就乱了方寸。
到了第三天,是出殡的正日子了,她又撑着病体出来,把如约叫到耳房里商议,“你和元直没有孩子,回头摔盆起灵,得议定个合适的人选。我这两天左思右想,把族里的孩子都仔细权衡了一遍,有个生母没了,父亲又续弦的,今年不过四五岁光景,可以过继到咱们家来,承继元直的香火。孩子小,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,你善待他,他知道好歹,将来不会顾念他亲爹。退一万步,就算他惦记本家儿,咱们还图什么,只要他孝敬你,不就足了吗。”
如约这才闹明白老夫人的筹谋,过继一个孩子,就意味着永远把她留在了余家,即便和皇帝不清不楚,也只能偷偷来往。将来皇帝爱屋及乌,受益的仍是余家子孙,那孩子冠的是余姓,这门庭就算彻底保住了。
其实这种心思,对她来说无伤大雅,反正自己早晚是要离开的。余崖岸等着出殡,得有孝子摔盆,这事儿迫在眉睫,反正没有别的选择,便点头答应了。
说是商议,其实是例行通知,因为孩子早就预备好了,披麻戴孝地被人领出来,先磕头认了亲,然后由人抱着,把一个瓦盆从高处砸了下来。
“哐”地一声四分五裂,早就就位的锦衣卫抬起棺椁,在浩大的哭送中,运出了府门。
送葬的队伍排得很长,每经过一处路口都有路祭。如约须得依例答礼,整个队伍走走停停,约摸走了有半个时辰,才进入余家祖坟。
余崖岸下葬的墓穴已经点好了,就挨着先头柳夫人的墓。他一直惦记着他的希音,希望他们一家三口能在底下团聚吧。
漆黑的棺椁落下去,落进幽深的土坑里,家仆挖起了头一锹土,沉甸甸盖在了棺盖上。如约低头看着,一股难言的酸楚忽然冲上鼻腔,她和他的恩怨也到此为止了,随着洒落的泥土,深深埋进了地底。
墓碑立好了,身上的孝服也得随着经幡和纸钱一起,扔进火堆里。取而代之是鬓边的白花,孝期足有一年,明年的今天才能摘下来。
跟着来送葬的亲友们,纷纷上前问候她,劝她节哀,要看开些。她点头说多谢,“府里预备了席面,大家回城吧。这两天多谢诸位亲朋帮衬,否则我手忙脚乱的,怕是不能仔细顾全。”
众人怜她可哀,都说着客套的话。这时候仆妇把那孩子领到她面前,引导着孩子,管她叫母亲。
她低头看,瘦瘦小小的人儿,眼神怯生生地,让她想起了今安。要是今安在,大概和他差不多的年纪,流落在外的孩子,肯定对这陌生的一切充满恐惧。所以她倒对他生出几分怜爱,他不肯叫人,她也不往心里去,阻止了边上频频催促的仆妇:“他还小,别逼他了。”
垂手向他招了招,“清羡,你跟我一起乘车吧,车上有果子,给你两个。”
那孩子犹豫了下,放开仆妇的手,转而来牵她的。一高一矮两个身影顺着小径缓缓往前,走进了一片浓阴里。
这场变故,就这么揭过了,接下来如约还和往常一样晨昏定省,只是有时候见老夫人呆呆坐在窗前朝外看着,恍惚了,会脱口问一句:“元直怎么还没回来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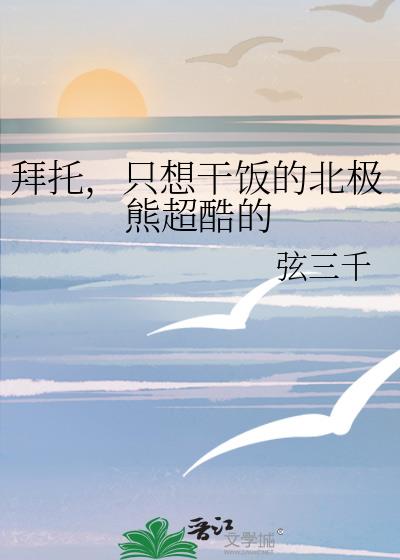

![[综英美]蝙蝠家唯一指定普通人](http://ylyynk.net/images/121/103331eb9ef981c0b8ac2f6742712b99.jpg)


![反派非要和我结婚[娱乐圈]](http://ylyynk.net/images/13/b7c3cfad87007dec58282e28da07f67e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