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月姚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半壶纱ylyynk.net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李朝夕进门先环顾一圈,站在离她八丈远的地方,冷冷笑道:“我还以为外面是谣传,原来是真的。”
“八姐请坐。”安宁语气平平。
“坐?我嫌脏了衣裳!你个不知廉耻的□□,他是你的血仇,你竟也忍得下去!”李朝夕胸口起伏不定,她们本应是一条绳上的蚂蚱,谁料李安宁扭头向仇人献媚,她恨李安宁膝盖软,但内心深处,未尝没有见人跳出泥潭的嫉妒。
茴香噌地站起来,回护道:“你再乱说话,我就把你打出去!”
“茴香,坐下。”安宁拿篦子一下下通头发,不再看李朝夕,“你不想去伺候皇上?”
齐皇宫里那位皇帝的年岁足够做李朝夕的父亲,当年又曾是她们父皇的手下败将,如今一朝翻盘,想也知道会对魏公主是副什么态度。
“我……”李朝夕确实是厌极怕极,可被明晃晃戳破,羞恼之下却忍不住嘴硬,“我就算死在路上也不会求你的!”
说完摔帘而出,茴香不屑哼声:“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,她以为自己还是高高在上的八公主呢。”
“她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,即便骤然遭难,一时半会儿又怎么改的过来。”安宁不以为意,篦子勾住发丝,扯疼了头皮,烛花爆了一下,安宁顿住手,问,“你刚才说什么?”
“奴婢说她还以为自己是公主呢。”
“不,前一句。”
茴香想了想,答:“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。”
话音刚落,茴香便看见安宁手中篦子落在地上,呼吸不畅地大口喘气。她急忙问:“姐姐怎么了?”
“你帮我打听小池院那边的事,尤其是李朝夕。”
——
最近季政忙着料理清算,安宁能躲多远躲多远。
茴香边绣荷包边说:“李朝夕很不安分呢。”
“刘爷爷从教坊司拨来教习,教她们弹琵琶,吊嗓子唱曲,学身段做派,其他人都乖乖学,李朝夕摔了琴,指着教习鼻子骂,被罚饿两天。”
毕竟是“贵人”,打是不会打的,怕留下伤痕,折磨人又不伤面皮的法子多得是。
季政回来用午膳,安宁在旁边装了小半个时辰的鹌鹑,见他去次间,瞅了个空想逃走,又被刘仓发现,他皮笑肉不笑地说:“姑娘,还不快去殿下身边伺候着。”
进去没看见人,里间屏风后传来声音:“拿件常服过来。”
安宁看刘仓。
刘仓咬牙:“快去啊。”这李安宁,有机会也不知道上,着实不中用。
从顶箱立柜里挑出件浅青色常服圆领袍,安宁低眉顺眼地给他换上。她感觉到季政的心情不错,却不知原因。
捋了捋腰间香囊下的流苏,安宁方直起身,冷不防被季政握住了手。
他翻过手面瞧了瞧,道:“冻疮怎么样?”
安宁轻声道:“谢殿下关怀,已不碍事。”
从季政的角度,只能看见她漆黑的后脑勺,头发上一根珠翠也无,耳垂珠圆润饱满,耳洞塞着米粒大的白玉耳珰。
刘仓看见太子握着李安宁的手从屏风后面出来坐在罗汉床上,琢磨着自己是不是该告退,却听太子道:“刘仓,你去叫小池院教习带人过来。”
他粗粝的大手握住她的,指关节的粗茧磨得她手心发痒。安宁贞静地斜坐在床沿,脊背挺直,余光瞥见季政在笑,心中有不好的预感。
不多时便有打扮艳丽的教习带上来一串十个美貌女子,正是那天在永巷中见过的诸人。
经过调教,这些女子的姿态和普通人有了很大区别,她们虽然只是站在那里,却横生一段风流情致。
刘仓叫王教习说说这些女子的专长。
王教习还以为太子要挑几个人留用,卖力推销道:“禀殿下,江眠的琵琶技艺精湛,一点不输教坊司的姑娘。秦蓁原先是官家千金,擅书画,懂音律,知书达理。还有李朝夕,一手萧笛无人能出其右,更别提此女的花容月貌,比之金霖江上的花魁师红玉也不遑多让。其他姑娘也是各有所长,定能伺候好主子。”
“安宁,”季政把她拉入怀中,纵容地问,“想听什么?让她们演奏一番。”
从前面投射过来的李朝夕的目光,仿佛要把安宁灼烧致死。安宁不想点名,季政眼神深似一汪水潭,她知道自己不点,季政绝对会让李朝夕吹奏。
“奴婢小时候曾听过一次《塞上曲》,婉转明澈,甚为动听。”
唤作江眠的姑娘立刻抱着琵琶坐下,素手沉稳地拨弄琴弦,丝弦声娓娓流淌,曲韵悠长。安宁听得出她不仅功力深厚,而且拿出了看家的本领。
一曲弹毕,江眠抬起眼睛看向长相俊雅的太子,希望对方能开口留下她。与其离乡离土去远在千里之外的齐皇宫伺候一个老皇帝,她宁愿留在东宫。
“你觉得如何?”季政揽着她的肩头,认真询问,好像她的评价多么重要。
“珠落玉盘,流音婉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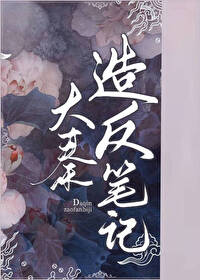
![此刻,我即为王[西幻]](http://ylyynk.net/images/406/5e25cd14b4b463f1188424858222e3d5.jpg)
![天才操作手[全息]](http://ylyynk.net/images/1657/569539f7c886a07d045d2a98d3605d42.jpg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