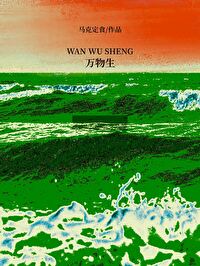去蓬蒿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半壶纱ylyynk.net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她对看旧人落寞没有太大的兴趣。更宁愿旧人永远陈旧下去。
他是跪在地上当狗,还是站着当主子,都别出现在她面前了。瑾王问她为什么难过。
青蘅笑:“哪有。”
她说她只是有点害怕,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帝王,若是失了礼降了罪,那可怎么办。她笑得太虚浮,太虚幻,看起来更接近于痛苦,而非自在。
瑾王道:“别骗本王了。你到底是念着成了太监的原主子,还是不想嫁给我。”“你能去哪?”瑾王突然抚上她脸颊,“你有把人逼疯的本事,可有时候,你什么也做不到。”瑾王的目光爱欲流连,却又有一丝恨。
恨她,更恨自己。
坐视她的丈夫被逼走,陪她去追她的丈夫,喂她药,带她来京城,计划与王妃和离,要给她名分,桩桩件件……有哪一样像他能做出的事。说给从前的他听,恐怕要惹得他笑出声来。
荒唐、可笑。
“不可理喻。”青蘅退后一步,看着他,“你不是最骄傲了?一副吃醋的模样,不像你。”“我?”瑾王笑,“我知我,明白我,珍重我,却不明白你。”
“你脸上出现的神情,并非因我,又是因谁?”瑾王静静地看她,好半晌才道,“说谎骗我,遗憾我不是个蠢货。”青蘅坐到床榻上,说自己累了,要瑾王离开。
瑾王笑,没出声,只是安静的笑。
青蘅讨厌他这副样子。
“是,我是想到赵元白了,你能怎样?杀了我?”青蘅推开他,“走啊,别在这里碍我的眼,你以为你是谁,你有权有势,我就不能拒绝你?”“我……我讨厌你,连我脑子里想什么你都要占据,未免太嚣张了。”青蘅推着他,赶他走。
瑾王忽然抱住她,无论青蘅怎样推拒,瑾王吻了下来。
不容抗拒,不准抗拒,青蘅渐渐失了力。
瑾王这辈子第一次吻一个人。
不是两情相悦,全凭他自己。
他多想学着赵三,把青蘅关起来,谁都见不着,只能看见他。越是相处,越是挣扎,越是不甘。或许当初,该把她送走的。
天下大势、朝堂风云,他该关心的那样多,为何把心思放在青蘅身上。这等被唾弃的做派,到底什么时候染上了。汤城是污.秽的泥城,不过去了一趟,捞出颗珍珠,人却成了泥腿子。
荣华富贵养就的风雅,碎了一地。
他竟也跟强盗似的了。
唇齿相依,瑾王渐渐失去了精神的挣扎,彻底沉溺进去。
而青蘅累了,挣扎不动了,她放纵着躯体,纵容他流连。
还好有寒风,还好是冬日,在衣衫褪尽之前,她推开了他。青蘅面上什么神情都没有了。
空茫茫的。
像大地的雪,冷白遥远。
她摸摸眼下,干的,没有泪可流。
她搂紧衣衫,轻声道:“夜好晚了,我该睡了。”她要到梦乡里去,而不是糊涂的情海。
瑾王的唇是红的,很红。
眼眶也红,一点点。他侧过脸去,不再看她。
连道别也嫌多余,瑾王走了,阖上门,关上风。他靠在门外,安安静静望着黑压压的天。想要拥有的,大部分都拥有,不该拥有的,他也不贪心。
唯独在她面前,失分寸、无廉耻、消道德,只余个哀,尚飨。
青蘅躲了王妃好几日,今日礼佛她却来了。
跪在王妃身旁的蒲团上,看向面前的金佛。
她问王妃:“这是真的金子么。”
太闪耀了。
王妃答:“为帝王祈福。真的。”
青蘅突然笑:"若我偷了它,逍遥自在远逃,佛祖可会怪罪我。"
她不用袍,在她眼里,这就是块大金子呀。
佛祖怎么会住到这金身来。
王妃摇头:“佛祖不会,帝王会。”尘世之外的佛管不到尘世之内的躯体。唯心而已。
“皇帝可真坏,”青蘅说,"他拥有整个天下,却连这座金身都舍不得。"“你呢,"青蘅问,“你舍得么。”
王妃静静望她侧脸,看她唇微微地嘟起,赌气般不满。
淘气。
王妃倏然拔出剑,问青蘅,要哪一块。佛祖的手,佛祖的心,还是佛祖的脑袋。青蘅惊得整个坐到蒲团上:“你不怕?”
“佛祖割肉喂鹰,岂会怜惜尘世里金银。若你需要,袍自是舍得。”
青蘅说:“那你岂不是慷他人之慨了。”
王妃道:"是。"
她回答得干净利落,毫无道德的羞赧。仿佛她是盗贼是匪徒还是圣人,都无关紧要。她不在意。好一个从心的和尚,竟不被清规戒律束缚。
“你说你要出家,你不敬佛祖,就算袍不在意,袍尘世的子弟也会不在意吗?”“我的庙,在我心中。”王妃持剑道,"无需他人提供修佛之所。"
青蘅突然笑,笑得倒在蒲团上。